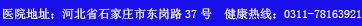海波书房下沙烧卖之外,还有鹤沙千
2024/8/20 来源:不详说起“下沙”,许多上海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下沙烧卖。尤其是那手工擀制的超薄烧卖皮,以当季新鲜春笋、鲜肉和秘制猪皮为馅料的笋肉烧卖,着实鲜美无比。事实上,比起各地开花的小笼包,起源于明代的下沙烧卖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菜,作为上海浦东南汇地区的代表小吃,如今它的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。下沙烧卖虽出名,但除地名之外,“下沙”二字所蕴含的更多意义,或许连大多数上海本地人也鲜少了解。近年来,我的好友胡龙昌一直致力于还原下沙曾经的那些故事——鹤沙文化的整理研究与传播,在一众人的奔走后,便有了如今我手边这本《鹤沙千秋》的出现。一个地名的由来,往往蕴含着一段过往的历史或是引人入胜的故事。下沙,是浦东成陆较早的地方,是南汇的“根”,而这片土地在古时的另一个名字称作“鹤沙”。巧的是,这两者的上海话发音也是相同的。而今“下沙”两字中不见了鹤的影子,随着时光流转,也让人渐渐忽略了这片土地上许多有关鹤的记忆。古时,东海沉沙渐次堆积形成沙滩,沙滩初成时,人烟渺茫,只有白鹤等海禽水鸟在此繁衍生息。年前,晋朝时期,滨海的村庄因产白鹤而被叫做鹤窠村,亦称为鹤坡。据《南汇县志资料》记载,“村头一排参天的古柏,有漠漠平沙的海岸,是白鹤的故乡。”鹤一直备受中国人的尊敬喜爱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。而作为备受世人称颂的华亭鹤的产地,鹤沙的鹤文化就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东吴名将陆逊的养鹤处就在鹤沙;陆机“欲闻华亭鹤唳”的感叹亦指的这里;北宋科学家沈括认为天下之鹤除了鹤沙(鹤窠村)的之外,其余皆是凡品;王羲之、李白、刘禹锡、白居易这些著名诗仙们都倾心于鹤沙产的华亭鹤,并留下诸多旧事与诗句……在鹤沙这片土地上,围绕翱翔云间的白鹤,实在留下太多美丽的传说、珍贵的历史往昔、精粹的文化艺术佳作。除了鹤,下沙还承载着盐业发展的辉煌记忆,更有“一部浦东史,半部盐业史”之说。早在隋代,下沙就已有人煮土盐,至公元年左右,下沙盐场已居华亭各盐场之首。南宋建炎年间(-年),朝廷在下沙建盐署并设盐监。元明两代,下沙盐场进入鼎盛时期,盐业经济高度发达。下沙因此成为“商贸咸集,遂成都会”、“歌楼酒肆、贾街繁荣”的商贸胜地,甚至成为当时国家经济支柱的重要基地之一。翻读这本《鹤沙千秋》,让我有机会深入看到了浦东往昔的另一面。史料的详实整理、传说故事的丰富记录,使得这本书读来趣味横生。从地区建制到地名传说,从文人诗咏到民间歌谣,从源出民间赶集贩盐的舞蹈“卖盐茶”到世代把持下沙盐场的瞿氏一族旧世事……鹤文化的浪漫抒情,盐文化的沧桑演绎,多样的雅俗文化曾在这里蓬勃发展,为鹤沙文化奠定了厚重而绚丽的基调,这是下沙的过往,更是浦东的矿藏宝藏。如今,当一座座博物馆美术馆进驻,一场场艺术文化活动接踵而来,浦东的文化新面貌不断让人惊喜、欣慰、充满期待。以往,大家常说浦东没文化,这是一种刻板印象。除了今人的努力,浦东实则早就留下深远悠长的文脉,但只有让更多人了解它的故事,努力地发掘、不断地传承,精心地浇灌和养护,我们才能真正“守住文脉,留住乡愁”。鹤沙的千秋是迷人的,更应是生生不息的。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,希望在一品下沙烧卖的同时,更多人能感受到下沙、乃至如今浦东这片土地上、那千年鹤沙文化所具有的超凡魅力。